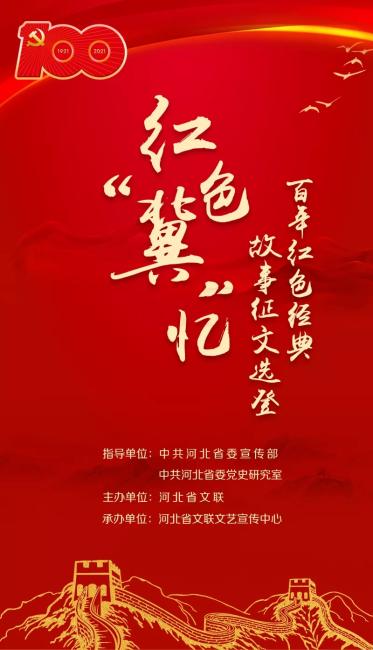
易家庄往事
齐建伟
这里是太行山腹地。
绵延横亘的群山,如同静坐村头缄默不语的老人。人们大都叫不上他们的名字,或许他们就没有过名字。“马武寨”,是他们当中不起眼的一个。山下的胭脂河如同一条银带,若隐若现在太行山的褶皱里,奔流不息。
太行山下、胭脂河畔,坐落着我引以为傲、一生依恋的家乡——易家庄。
为了脚下这片土地
清明前夕,站在村头那片绿茵初现的土地上,身边是各式新建的房屋,还有一家在建的养猪场……新翻泥土的气息和着青草芽子的味道,恣意撩拨着我的心绪。
眼前不停忙活的老胡,有一搭没一搭地回答我的疑惑。在他面前的一块红布上,稀稀落落地放着些已辨不出形状的骨头,不远处是他用木板装钉的木匣。他神情肃穆,目光凝重,埋头仔细在泥土中翻找着,像是在用粗糙的大手过滤逝去的岁月。
老胡就是易家庄本村人,七十多岁。他的父辈兄妹五人,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演绎了非凡的革命人生。
老胡的大伯父胡步三,1924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,是阜平县早期的中共党员之一。他毕业于黄埔军校,组织参加过上海早期的工人运动和东北抗日联军,解放后曾在铁道部任职。在他影响下,三个弟弟、一个妹妹都相继投身革命。
老胡的父亲胡步良在兄弟中排行第四,1937年参军投身革命。当年,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设在城南庄;北方局、荣臻子弟学校、边区医院等,先后都曾设立在易家庄村。说这些时,老胡起身抬手,为我指点着村里或旧或新的参差院落:“这是学校、这是医院、这是食堂……”他厚厚的嘴唇颤抖着,浑浊的眼睛里闪着亮光。我的目光跟随他拂过这熟悉而又满是故事的村庄,心潮不禁汹涌激荡起来。
胡步良作为边区政府的通讯员,曾奔走于边区政府各个机关之间。因他属正规军,懂得爆破技术,还参加了易家庄村的游击组。
1943年9月,日寇“扫荡”到易家庄一带,胡步良和游击组长刘应法及数名队员,在村头埋设地雷阻击敌人,掩护群众撤退。后与敌人交火,退守马武寨山,在歼敌20多人后,被围困在山顶的石洞中。一番血战,子弹打完了,鬼子威逼没能逃脱的百姓搭梯子爬上洞口“掏人”,其间先后有两人摔死。为了避免乡亲们再次伤亡,也为了不当俘虏,游击队员们聚在一起,傲然挺立,誓死不降,组长刘应法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。由于土制的手榴弹威力有限,刘应法英勇牺牲,组员胡步良、魏殿才、杜云起、张希文受伤被俘。
鬼子押解他们来到灵寿县排房村,一路上百般折磨,挥鞭抽打,不让吃饭,逼迫他们说出八路军粮食所在地,队员们闭口不答。狡猾的鬼子从胡步良手上的老茧看出他并非普通游击组队员,于是对他严刑拷问。胡步良始终缄默,鬼子恼羞成怒,残忍割下他的半拉耳朵,还用脚搓成了肉泥。鲜血顺胡步良的脖颈流下,染红了身上的老棉袄。丧心病狂的鬼子眼见阴谋不能得逞,就把辣椒水和着大粪汤灌进胡步良的口中,肚子上再压块大板子,两边有人使劲儿压。辣椒水、大粪汤、血水从他的鼻子、嘴、耳朵里流出……
说到这里,眼泪从这个北方汉子沧桑黝黑的脸上无声滑落。他用厚实的手掌抹了一把脸,说:“我爹走后,多年不唠叨这些事儿,都快忘了,真是愧对那些死去的人们!”
在敌人准备杀害他们的前一天晚上,一位当地的伙夫,利用送饭机会给胡步良他们送进两颗大铁钉。他们在关押的土坯房墙上挖了一个洞,利用房后羊圈作掩护,成功脱身。
因为刘应法小名儿叫“四秃子”,从那以后,晋察冀边区政府便将马武寨山更名“四秃子山”。
说着话,老胡扒拉出一块较大的碎骨,小心翼翼地放到红布上,边整理边说:“多年听不到我爹唠叨,这些事儿都快想不起来了……”
老胡轻轻地摇着头,嘴里喃喃重复着这句话,一阵“吭吭”的咳嗽淹没了他的话。
就在我走访老胡几天后,远在山西省天镇县定居的老胡八十岁高龄的大姐,通过家人寄给我一沓——整整38页,关于她父亲革命经历的手抄稿。留言中写道:“我现在什么也写不了了,过去的事儿大都想不起来,说话前言不搭后语。如果能让更多人知道这些事儿,也算了了我的心愿。”
值得几代人拼命守护、流血牺牲、夙夜牵念的,也许只有脚下这片土地了。
不能亏待革命首长的后代
“小小灯儿没有油,丈夫打仗把俺丢,缺吃少喝也不愁,做件衣裳美悠悠。胭脂河水清悠悠,种地支前不落后,赶走鬼子乐悠悠。”
老胡边哼边说,小时候他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。母亲无论是油灯下做针线活儿,还是哄孩子们睡觉,都喜欢哼这首歌。
“我娘也是党员!”老胡忽然抬高嗓门说,语调中明显添了些许骄傲,“我娘个儿大能干,挑个百十来斤粮食,上房都没问题。”边区政府驻在易家庄时,老胡的母亲不光送军粮,做军鞋,还用奶水喂养过一位八路军首长的孩子两年多。
孩子名叫“胜利”。老胡的大姐两岁时,又添了二姐。胜利的爸爸在石家庄指挥作战,妈妈也在部队工作,嗷嗷待哺的孩子不能带在身边,老胡的母亲便主动承担起喂养孩子的责任。奶水不够,她每次都是先让胜利吃好,再喂自己的孩子,直到胜利的父母把他接走。
一阵轻风吹过,听着胭脂河淙淙的水声,我仿佛听到了隆隆的炮声,看到了老胡母亲在山上劳作、在河边洗尿布、在院里敞怀给胜利喂奶的身影……
老胡的二姐体弱多病,两岁时就夭折了。“村里那个老光棍儿就是用这个粪篓子,把你二姐背出去埋了的(村里旧俗,夭折的孩子都由没儿没女的人去掩埋)。”老胡说,她母亲晚年经常摸着那个粪篓子叨叨这句话,每次都泪流满面。哭完了,再哼唱那首哼了几十年的歌。
老胡说,从鬼子那里逃脱以后,他的父亲由于当年受刑的缘故,肺一直不好,最终因肺气肿而离世。他母亲临终还念叨着夭折的二女儿,还有那个叫胜利的孩子。
“不过我娘说了,喂养胜利这事儿她从不后悔,她是不能亏待革命后代的。”老胡接着说。
慢慢扒拉着新捡起的一块骨头碎片上的土,老胡轻轻地说:“知道这是什么吗?”我茫然地摇摇头。“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?”他指着脚下的土地问我。
乱葬坟!这个地名倏地闪现在了我的脑海。一时心里很不是滋味,时光竟然也模糊了我的记忆。“多年不唠叨这些事儿,都快忘了,真是愧对那些死去的人们!”老胡的话,此刻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。
乱葬坟
上小学时,每逢清明,老师都会带我们拿着笤帚、铁锨来这里扫墓。这个叫作“乱葬坟”的地方,密密匝匝有着几十座很小很小的坟堆。听大人们讲,易家庄村小学所在的地方,当年是边区医院,前线下来的伤员都在这里救治。许多战士牺牲后,尸骨都留在了胭脂河畔的这块土地上,刘应法也葬在了这里。
村里人给这块地取名“乱葬坟”。
爷爷给我讲过,那个年代缺医少药,有时候甚至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给伤员做手术。他们就曾趴在医院窗户上,偷看给没用麻药的伤员“锯腿”——做截肢手术。百般努力终没能留住年轻的生命,爷爷说那个孩子是“疼”死的,于是“乱葬坟”里添了一座新坟。
在以后的日子里,每次路过“乱葬坟”,我的敬畏之情就会油然而生。
沉郁平和的岁月,让行走其间的人们渐渐变得“懒散”起来,一代代孩子们知道“乱葬坟”,却很少再听到“乱葬坟”的故事。前些年,村庄扩建到“乱葬坟”一带,计划建新房。村里一位奶奶说,每天晚上都会梦到有穿军装的人去给她家挑水,扫院子。人们信她,因为人们忘不了“穿军装的人”。
于是,村里人自发组织,把这些无名的坟茔,一座一座迁到了山上。
后来,国家有了烈士纪念日,每年这一天,举国上下都会祭奠先烈。2020年,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之际,许多散落在朝鲜战场、异国他乡的烈士遗骸,被接回了祖国。他们终于“回家”了!可“乱葬坟”里的烈士们,依然静静长眠在这里,不知道他们来自哪里,更不知道他们是谁。
前一阵儿,这里新建养猪场,听说又陆续挖出了人的骨骸,老胡就经常来这里踅摸着找寻。烈士们把热血洒在了易家庄这片土地上,老胡觉得自己必须一个不落地“找回”他们,好好地守护他们。
“他们都没有留下姓名,可他们把命留给了我们。他们还是孩子,爹娘找不到他们了,我们不能丢下他们。”老胡摩挲着身边的木匣,嘴唇哆嗦。
是啊,“乱葬坟”里安葬着刘应法,安葬着失去腿的战士,安葬着许多无名烈士。这里没有纪念碑,眼前的马武寨、逶迤的太行山就是他们的纪念碑,而历史的记忆是永久的碑文。
每个人心中都矗立着一座山,流淌着一条河,安放着一个村庄。我们应该给记忆腾出一点空间,让那些英雄的名不见经传的山脉、河流、村庄,映入心田,永不忘怀。
老胡俯下身子,吃力地抱起安放烈士遗骨的木匣,步履蹒跚地走向远处的山坡。一队红领巾也在老师的带领下,从易家庄小学出发,手捧菊花,走向那面山坡。
热乎乎的阳光轻拂着那些老人一样的山山岭岭。我想,可以给老胡的大姐回话了。
(齐建伟,阜平县城厢小学老师,保定市作家协会会员。)



